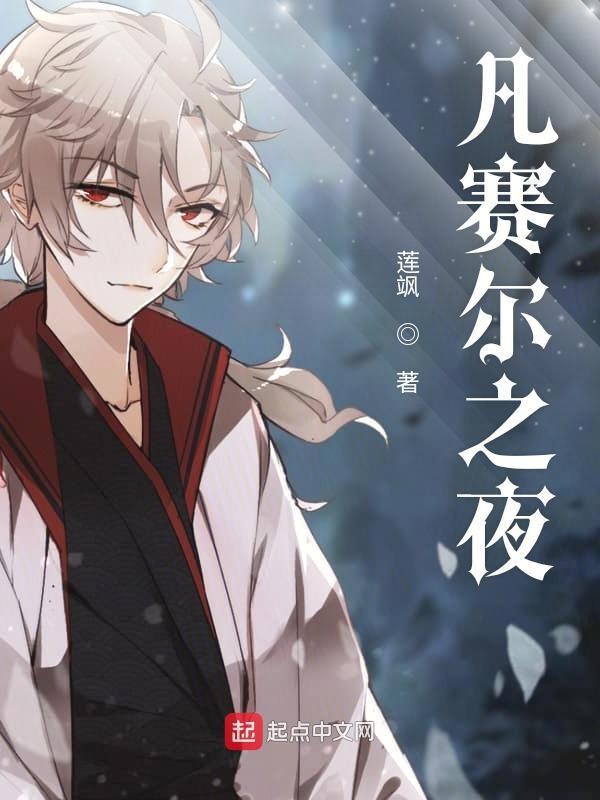爱来阁>假如父母只是一份工作 > 第138章(第1页)
第138章(第1页)
纪梧说:“倒也不是应该,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说法的话,我觉得是‘正常’。打个比方,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孩子,我是会那样做的。”
她停顿一下,又说:“不过我的想法不具备参考性,因为我没经历过那些事,与其说我是为了孩子去做,不如说我其实是在自己补偿过去的自己。”
这个逻辑是能说得通的,而且很正常。
张亦可闭了闭眼睛,问纪梧:“那我为什么会觉得应该呢?”
“我没有要向你炫耀的意思……”张亦可认真说明了一下,看到纪梧点头后继续说:“可我从小到大,我爸妈都是很自然地去为我做那些事情,从来没有抱怨过,也没有不耐烦过,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有多么不容易,也不觉得这些记忆有多重要。我是被这样熏陶着长大的,我不是更应该在以后去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做这些吗?可为什么我只要一想起那种假设,就觉得哪里都不对,甚至烦心得不得了?”
纪梧微微睁大眼睛,又听到张亦可说:“而且,我居然会觉得,父母就是应该为了孩子去做一切事情的……”
张亦可看着她,睫毛忽然簌簌抖动几下,“你知道吗,我自己是不认同这些的。可为什么换成我父母对我,我就觉得是‘应该’?而且,我竟然是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些的,这太不对了。”
纪梧呼吸乱了几下,诚实道:“我也不清楚。我没有经历过。”
张亦可更加迷茫了。
有那么一瞬间,她甚至怀疑,自己这次和父母吵架,错误的地方就是在自己。
是她太过独断,不识好歹,拒绝了父母的好意。
但这种想法仅仅只有一瞬间。
张亦可实在无法说服自己,那个表里不一的什么凯的出现,是她父母为了她好的表现。
这很离谱。
张亦可在这一刻变得极其矛盾。
她一面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,一面又觉得自己的心理想法不可理喻。两种情绪杂糅在一起,张亦可感觉自己对也是错,错也是对。
她无法区分自己到底哪里是对,又有哪里是错。
但其实只要她平静下来仔细思考,就会发现,这根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,于是也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两件事情归结到一起,得到那个唯一的有关于对错的答案。
可偏偏,她这时候心里太乱了。
张亦可晃晃脑袋,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只思考这个世界的一切,她问:“如果手抄报没有完成,会有什么惩罚吗?我会被记一次失误?”
“你没完成?”纪梧问。
“太难了,我们就凑合着做出来一张。”张亦可说:“那一张还是特别草率的那种。”
“那个东西是要送去评比的,最基础的是合格与否,不合格就打回来。”纪梧叹了声气,“总之这是一定要完成的,不至于被记失误,但是会不断打回,直到你合格的那天。”
张亦可如遭雷劈,面无表情地听完了这段话,最后安详闭眼,“我想死。”
纪梧给她倒了杯水,努力地尝试安慰她:“其实这种处理算是比较柔和的了,我们当时才是恶心死了。哪个学生的手抄报不合格,就要被老师在课堂上面点名批评,严重的还会被张贴到教室外面展示栏被很多人看和嘲笑……”
张亦可睁开眼睛,看着纪梧,无声须臾,张开双手抱住了她,心疼地说:“不要把自己的伤痛经历拿出来安慰别人啊。”
纪梧回抱住她,在她后背上拍了两下,“其实我已经不太在意了,但是好像也没有安慰到你。”
张亦可心想我要是就这样被安慰到,那我真是人品有问题。不过经过这么一出,她确实没心思再想自己之后要遭遇的磋磨,只是心疼纪梧的过去,同时又想起那该死的手抄报。
她现在已经不再只是思考这个世界了,而是对于现实世界也开始思考。
在评选以及点名批评并且张贴到展示栏这种行为的存在下,手抄报是否真的有必要存在?
并非每个人都具备艺术创作力,那么这种需要此种能力的作业又是否应该存在?
张亦可认为不应该,或者说,不应该以这种形式存在。那样一来,至少纪梧这样本就不幸的人不会再遭遇另一种不幸。
而且,对于自己来说,张亦可也实在是很认真地认为,这种东西,根本就不是布置给她的。很明显她做不到,那就只能是她父母来替她完成。
从前她认为这样理所应当,现在换位思考,张亦可觉得这种行为大错特错。
假如她是父母,她真的会烦不胜烦。
如此一来,张亦可又觉得,她父母对她是真的很好,特别好。
张亦可愧疚心起,忐忑又期待地等着周一的到来。
周一下午三点,张亦可和刘宇凡来到工作地,接到了他们那个被打回来的任务——五张手抄报。
两人安静对视瞬间,眼中尽是惆怅与无奈的悲伤。
半个小时过后,两人才真正拿起笔,准备动工,不想筹备半天,最终不约而同画出来一个圆。
目光再度碰撞,张亦可问:“你画的什么?”
刘宇凡不假思索:“太阳。”
又问:“你画的什么?”
张亦可:“……太阳。”
“……”
一阵无言,两人默契地拿开纸张准备重画。
十分钟后,两人不约而同画下一道波浪线。
目光碰撞上,两人迅疾躲开,以百米冲刺都追不上的速度把手下纸张甩开扔掉,低头,握笔,正襟危坐,眉头紧锁。